又一个较为焦灼的年到了,因为疫情,好多人还是无法顺利回家团聚,暂且称之为今年过年的一“关”。
年关一词,近些年已经很少提起。原来称年为“关”,是因为物质生活的极度贫瘠;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,年已经不能算作“关”了,所以鲜有人再提及。
像我这个年龄的大部分农村人,都听过或看过以《白毛女》为代表的凄惨除夕的情景:“旧历除夕,杨白劳终因无力偿还重利,被黄世仁威逼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押。杨白劳痛不欲生,回家后饮盐卤自尽。”对于杨白劳和相依为命的喜儿来说,这个“年关”已经不是简单地过不起年了,而是人生一大关了。好在这部戏还有两个点值得人们为之确幸,一是如此境遇的生活下,杨白劳还不忘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,父女情深可见一斑;二是最终喜儿和大春的终成家庭。
《白毛女》描绘了建国前一个有代表性的年关场景,无关现在。只是年关这个词让我想起了这部戏而已。
一
我的小时候,已经是四十年前了。每逢过年,无非是想放放鞭炮;除夕夜打个灯笼,在自己家和爷爷、叔叔大爷家之间来往穿梭。那时候放鞭炮,没钱买,怎么办?当然是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(毛泽东于1939年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)。“擀鞭”,就是做鞭炮,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。临到过年,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擀鞭的过程。擀鞭的设备是木质的,主要分为两大部分,放到地上的凳子和板凳差不多,比板凳高、短;另一部分是倒“丁”字形状的,用铁丝吊在屋里的一个檩条上,垂下来落在凳子的上方,中间的些许空间决定鞭炮的粗细、大小。用旧的报纸或书纸,裁成想做鞭炮的大小,缠在一根粗铁丝上放到凳子中间,然后用倒“丁”字型木质工具往前一擀,用胶水粘住纸卷,鞭炮的筒子就做好了。再就是用泥巴堵住一头,中间充上鞭药,另一头挤上芯子,一个鞭炮就做成了。最后把一个个鞭炮用编辫子的方法编在一起,根据需要编成数量不等的挂鞭就可以挂起来放了;当然,需要出售的话,还要用纸包起来,便于存放和运输。就这么简单的设备,当时村上也就一两户人家有,用它做的鞭炮,大部分还是要拿到鞭市上去卖的。
鞭市,一般是腊月廿以后,临年靠近出现在各大集市上专门用来卖鞭炮的一片集中开阔地。现在已经记不清鞭市消失的年份了。在鞭市上卖鞭的既是鞭炮的制作者,又是经销者。买的、卖的都聚集在这里,人山人海。卖鞭炮的,为体现自家的质量好,各家各户一边放一边卖,嘴里还大声吆喝着,甚至声嘶力竭。他们放的鞭炮可不是小的,都是选大的放,小的根本听不见,所以一家比一家放的大,一家比一家放的响。为了吸引买者,有的甚至把一挂鞭拿在手里,点燃药引后,一手捂着耳朵,另一只手举着,侧身来放,显示卖者的勇敢。买鞭炮的,听到哪家的响,人群会跟着动静一窝蜂似地往那里拥。然后,疯狂地抢购,怕是慢了会买不到。
鞭市很热闹,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年味。但当时买鞭炮,一家也就舍得买上两三挂,年三十晚上、初一中午和初二上坟的时候放放,其他时候小孩子是没得放的。因为过年,家里还要买上二斤肉用来包饺子,还要准备走亲或来客人吃的、用的,那时几乎没有积蓄的农村家庭,过年确是一关。
二
当人们腰包渐鼓,有了钱以后,其思想和行为会随之发生变化,过年的方式当然也会变化,还是拿放鞭炮来说。以前是没钱买鞭炮过年,后来是过年买鞭炮成为一种“竞赛”,这话说来也得是近20年前开始的。年三十晚上和初一中午各一顿饺子,也就两挂鞭的事儿,放完就可以吃饺子了。让放鞭炮成为一种“竞赛”,是年初二一早上坟的时候,基本是发生于同一家族之间。虽是同根同祖,但随着时代更迭,本是一个祖坟的同一家族,越来越多故去的人也会逐渐另立坟头,成为家族分支的另一处祖坟。到了初二该上坟了,各个家族分支的子孙们,有的推着小推车,有的手搬肩抗,还有的开着着“三马子”拉着改良后的鞭炮——开天雷;到后来有了私家车之后,也有的直接把开天雷装满或大或小的车辆,一直开到老祖宗的面前。
上坟当然是先烧纸,除了自家祖上坟前多放些纸钱外,其他不知是哪位先祖的坟前也分别放上一张,算是过年的“见面礼”。纸钱烧起来后,下面就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了。当一家的开天雷放起来后,窜得高,响声脆,便会引来人们、或羡慕、或嫉妒的赞美声;当有的开天雷窜得没那么高,也没那么响,甚至出现了哑炮,人们便会哄堂大笑,嗤之以鼻地说:“这是嘛玩意儿啊!”
这种你追我赶地争相在老祖宗面前表现的场景,直到2019年因环境保护的原因,被政府叫停,且现在已经是全境全时段禁止燃放烟火爆竹了。像这样的“竞赛”,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。其来由应该是人们走出家门,脱离开“庄稼地”后,通过在外务工经商开始挣了钱,也或许是在外见识过经济较发达地方人们放鞭炮的方式,逐渐“引进”到了当地。
就是这种上坟放鞭炮的方式,看似热闹,给老祖宗增脸,其实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家庭来说,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。就连年轻人的父辈们,每到年底就交代给自己的儿孙,上坟的时候能多买一点儿开天雷就多买点儿,别让人小瞧了。当然也有的父辈深明大义,理解子孙的日子并不宽裕,就嘱咐适可而止,上坟有个意思就行了。但是无论父辈们怎么说,当儿孙的也不想落到哪家后面,没有最好只有更好。每年买鞭炮的钱也越花越多,就像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速,每年以一定的百分率在上涨。
这无疑又是过年的一个关口,不仅经济上的,还有精神和面子上的。感谢现在的环保政策,让大部分人们度过了这一“关”。
三
现在农村的男孩子找对象不容易,原因也不全归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性别比失调,这应该还有社会进步的因素在里面。比如男女平等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重视,农村女孩子不再甘心婚后常年在家看孩子做饭,等自己的男人挣钱养活自己。她们需要工作,需要和男孩子一样走南闯北。当她们步入城市,自然会被城市的环境所吸引。虽然干的工作也会很累,但累的同时她们能感受到农村没有的设施、环境和自由。再就是现在农村家长对女孩子的教育比对男孩子的期望值更高,希望她们能够上个好学,将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。这些女孩子进入城市务工或上学后,有的不再返乡,无疑给农村男孩子找对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
即便是这样,但每个男孩子总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意中人。当男女双方经人介绍或自己谈,处过一段时间后,一般是要带对方到自己家见见父母的。尤其是到过年的时候,男方总是要邀请女方来家里过年的。这几年听闻的少了,前些年大概是农村的一个惯例,且形成了规则。临到年底,男方家长就会督促自己的孩子,带上礼物到女方家,和女孩儿本人还有她们的父母商量来家过年事宜。
不要小看未过门的儿媳妇来家过年这个事儿,对于男方家长来说简直是“大考”。一来要准备给女孩儿的见面礼;二来要招呼亲门近支的婶子大娘、七大姑八大姨们到家来,还要摆上几桌。女孩儿一般腊月二十八九来,初二三回。就这几天,男孩父母尤其是准婆婆,累的腰酸背痛不说,生怕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,“得罪”了准儿媳和她的父母。给个脸色看看是好的;有的因为来过年,还真有散伙的。
这一“关”,着实让男方家提心吊胆。
四
新冠疫情的不期而至,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。
全国上下常态化的防控,已经能够较为迅速地遏止疫情的扩散和传播,并能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发生疫情地区的生产生活。这种局面的得来,得益于中国式的疫情防控,无可厚非。给人们带来生命健康保障的同时,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出行自由,尤其是到了过年,那些因为疫情回不了家的人们,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浮躁的。尤其是那些把孩子留给老人,夫妻二人在外务工的,有的每年也就过年能和父母、孩子见上一面。真的回不了家,心里的思念和委屈可想而知。对于全国一盘棋的疫情防控,一个家庭的不能团聚实在是不足挂齿。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能够团聚,就是他们过年的全部。
事不过三,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如此,也应该符合自然规律的演变。就像伏羲发明的卦象,只有三爻组成,即便周文王发展为六爻,也是分内爻和外爻,还是三爻而已。
疫情这一关,终归会伴随虎年的到来,烟消云散的。
今年的春暖花开,应该是真的春暖花开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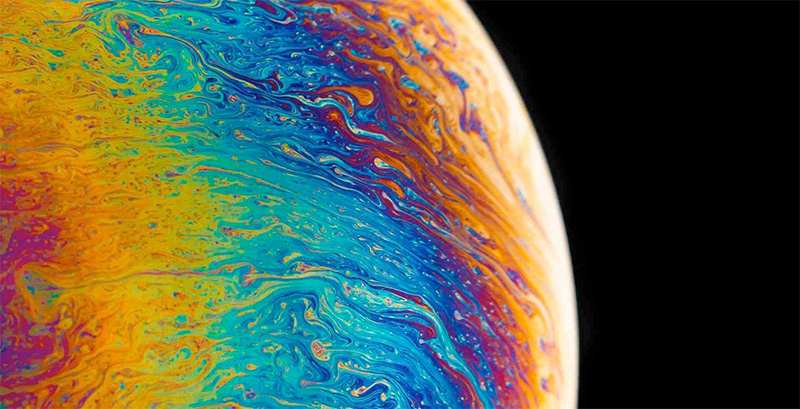
评论 (0)